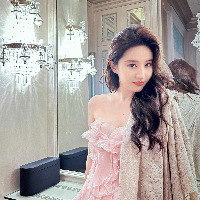《玫瑰的故事》:一出被浪漫包装的依附寓言
——当“成长”成了爱情通关的代名词,女性叙事还剩多少真实?
文 / Toni
2024年夏天,刘亦菲主演的《玫瑰的故事》掀起了不小的热潮。改编自亦舒1981年的同名小说,剧集借由黄亦玫从少女到中年的生命轨迹,试图描绘一幅“现代都市女性成长史诗”。然而剥开精致滤镜与明星光环后,我们看到的,不过是一位被爱情反复重塑、被男性频频托举的“完美女主角”。她的每一次转折、每一场蜕变,都绕不开男人的出场与退场。与其说这是“独立女性”的成长史,不如说是“情感依附者”的通关手册——只不过通关奖励,永远都是下一个更好的男人。
—
一、人生像开了挂,职场如童话,现实被一键删除
黄亦玫的成长路径,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角色扮演游戏:初恋失恋→获得港岛策展工作;婚姻破裂→转身成为畅销作家;灵魂伴侣病逝→邂逅年轻理工男追求者。每个节点都不讲过程、不谈代价,只讲“命运馈赠”。
她进入中环艺廊,不是靠作品、经验或人脉,而是前任庄国栋一句“我帮你打个招呼”;她从婚姻废墟中爬起,没经历求职碰壁、经济拮据、托儿无门,反而灵感迸发,出版小说一炮而红;她40岁带娃再恋24岁男孩,雨中表白感人至深,仿佛社会从无偏见、家庭从无反对、育儿从无压力。
这不是成长,这是许愿。编剧把现实世界的齿轮一一卸掉,让女主角只在情感轨道上滑行,从不跌倒,从不挣扎,从不计算成本。观众看着爽,但若误以为这就是“女性逆袭”的模板,那才是真正的悲剧。
—
二、她不是主角,是客体——被爱塑造的“玫瑰标本”
黄亦玫的情感世界如同一面镜子,映照出她所遇见的男人。庄国栋教她“爱是自由”,方协文让她“认清控制”,傅家明给予“灵魂救赎”,何西带来“青春回响”。她的“觉醒”,总是在被某个男人深刻爱过、放手过、托付过之后才姗姗来迟。
最讽刺的一幕,莫过于她站在天台喊出“我不需要谁来完整我,我自己就是完整的”——而这段独白,恰恰发生在她刚被一个年轻男孩热烈追求之后。她的“完整”,仍建立在“被选择”的前提上;她的“独立”,仍需要“被爱”作为认证印章。
母职?工具化了。女儿在离婚后“暂时寄存”前夫家,直到女主谈恋爱才“想起”自己是母亲。育儿责任、儿童心理、平衡困境……剧本选择集体沉默。友情?边缘化了。唯一敢说真话的闺蜜关芝芝,在说了句“你总在男人里找答案”后,迅速沦为“稳定无趣”的背景板——仿佛清醒女性注定无戏可写,只有陷入情感风暴的灵魂才值得镜头聚焦。
—
三、伪独立的糖衣下,是结构性逃避
宣传语高呼“女性为自己而活”,可剧本悄悄改写答案:“只要你够美、够优雅、够幸运,总会遇到一个更懂你的男人来拯救你。”
这背后藏着三重危险:
其一,把制度问题包装成运气问题。35岁职场歧视、离婚后的经济困境、母职惩罚——在剧中通通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“换个男人,人生重启”。
其二,把成长等同于换伴侣。每一次人生升级,都以更换男友为标志。逃离控制者是成长,遇见完美情人是成长,接受年轻追求也是成长——仿佛女性的命运剧本,始终由男性角色推动。
其三,制造温柔的麻痹感。观众看完感动落泪,以为“她做到了”,却忘了问一句:现实中,谁在替她付房贷?谁在陪孩子写作业?谁在深夜改稿时替她冲一杯咖啡?幻想太美,反而让人忘了去争取真实世界应有的制度保障。
—
四、四十年前的解药,治不了今天的病
亦舒的原著诞生于1981年的香港,那个年代,“女人可以离婚”、“可以为自己活”已是先锋之语。但今天是2024年。今天的女性,不再满足于“能走出婚姻”,她们要的是:离婚后孩子归谁、房子怎么分、工作还能不能找、再婚会不会被贴标签、中年转型有没有支持。
黄亦玫从不操心这些。她的人生困境,清一色是“情感困境”;她的解决方案,清一色是“换一个更温柔的男人”。这种叙事,像用缝纫机修理火箭——工具和问题根本不在一个维度。
—
结语:我们不要温室玫瑰,我们要旷野野草
《玫瑰的故事》拍得美,演得真,但它的内核,仍是旧瓶装老酒——用当代影像包装传统依附叙事。它让我们看到一个被爱包围的女人,却没让我们看到一个自我建构的女人。
真正打动人心的女性故事,应该像《我的阿勒泰》里在边疆寒风中坚持写作的李文秀——孤独、拮据、无人喝彩,却用笔记录生活,用肩膀扛起责任;像《不够善良的我们》中在婚姻疲惫里重拾专业的简庆芬——不靠爱情托举,而在废墟中重建职业尊严与母女关系。
她们不是玫瑰——不是被修剪、被观赏、被书写的对象。她们是野草,在现实的缝隙里,沉默而坚韧地扎根、蔓延、生长。没人给她们搭台,她们自己铺路;没人替她们写剧本,她们亲手执笔。
致所有仍在生活里摸爬滚打、拒绝被浪漫化、拒绝被拯救的当代女性:
你的价值,不需要爱情认证;
你的战场,不在男人西装口袋里,
而在你亲手开垦的土地上。你不靠谁托举,
你是自己的支点。你是野草,
却终将改写整片旷野的风景。
【完】
—
附录·台词碎影——理想与现实的裂缝
- “爱是自由的,我不觉得我背叛了你。”→ 伤害被美学化,责任被轻描带过。
- “你不需要成为谁的附属,你只需要是你自己。”→ 台词很美,但他仍在提供经济支持、情绪容器、甚至临终托付——言行之间,裂痕深不见底。
- “我不在乎你结过婚、有孩子,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。”→ 理想主义宣言,在现实面前如纸糊的盾牌——房贷、学区、婆媳、偏见,哪一样能靠“我在乎”解决?
- “你总在男人里找人生答案,什么时候才能为自己活?”→ 全剧最锋利的一句,可惜说这话的人,很快被叙事放逐。
- “我不需要谁来完整我,我自己就是完整的。”
→ 这句话,如果是在独自带娃加班到凌晨、咬牙付完下月房租后说出,或许才配得上“独立”二字。